安妮-雅莉多次重塑自我。然后是政治
在 2016 年决定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西澳考恩(Cowan)议席之前,结过三次婚的阿利已经过着复杂而有些杂乱的生活。她以最微弱的优势击败了自由党现任议员卢克-辛普金斯(Luke Simpkins)。
“她说:”计票花了 10 天时间。
2019 年,她的得票率有所提高,到 2022 年,她的得票率达到 46.9%,比 2019 年的得票率提高了 9 个百分点。
在第一次竞选中,她记得自己拿着一张照片站在火车站向汽车挥手致意。一年前的今天,她应邀在白宫举行的反恐会议上发言。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从白宫到绿林车站我都干了些什么?”
1967 年,Aly 在埃及亚历山大出生。她是一名护士和一名纺织工程师的女儿,两人于 1969 年移民到澳大利亚。二十年前,该中心曾因 13 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而成为世界头条新闻,如今中心的条件已得到了极大改善。
一家人先是搬到了悉尼内西区的马里克维尔(Marrickville),在即将搬到德克萨斯州的时候,他们又搬到了布里斯班,在那里,阿利的父亲在生产紧身胸衣和女性内衣的詹宁斯(Jennings)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他们的第一套房子是在非常不 “chi chi “的西区买的。
“1974年,洪水泛滥。我的父母来自一个沙漠国家,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阿莱说。
“但这是我们澳大利亚故事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因为我们发现的是一个社区。几乎就像他们通过这场悲剧成为了澳大利亚人。
她说,这样的时刻与同性婚姻公投、”声音 “公投以及纽约 “9-11 “袭击后难以遏制的种族主义等其他分裂和愤怒时刻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说,加沙目前的局势令人不安。上个月,阿利与埃德-胡西克(Ed Husic)一起警告说,加沙的 230 万居民正在因恐怖分子的罪行而受到 “集体惩罚”。
随着以色列-加沙战争变得更加分裂,Aly 说她正试图证明 “我们必须认识到彼此的人性,即使在我们受到最大伤害的时候,也要对彼此表示同情”。
“我曾与穆斯林社区和犹太社区的成员交谈和会面。她说:”我对这里有代际创伤、累积创伤和受到伤害的社区说的是,有时最难做的事情就是在一群受到极大伤害、唯一能做的就是大喊大叫的人中间发出理性、平和的声音。
作为儿童早期教育部长和青年部长,Aly 的工作非常繁重,她需要完成对儿童保育和早期学习部门的两次审查。
政府正在缓慢地向普及模式迈进。今年 7 月,政府将收入不超过 8 万元的家庭的最高补贴率提高到 90%,并对收入低于 53 万元的每个家庭实行滑动补贴。
“Aly 说:”事实上,澳大利亚是幼儿教育和保育费用最昂贵的国家之一。
“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质量体系和已实施 10 年的质量框架。问题在于成本,以及市场并不像你期望的那样发展。不是哪里有需求就去哪里,而是哪里有钱就去哪里。
生产力委员会本周发布的报告以及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调查将确保儿童保育问题在未来几个月内仍是阿尔巴尼塞政府的热点问题之一。
政府已委托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哄抬物价。
“我们将继续关注。Aly 说:”那些在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领域大肆敛财的人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关注他们,而他们的代价是,家长们无法负担得起、无法获得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
她说,从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上市的公司到爸爸妈妈的小企业,系统的复杂性使其难以驾驭,但她的目标是找到一个 “适合所有人 “的系统。
“这可能意味着在不同地区提供不同种类的服务,甚至是不同种类的服务。但这是家长对孩子的质量和安全有信心的地方”。
大多数人都会对阿莉感到熟悉,即使他们还没有把名字和面孔联系起来。她就是在提问时间坐在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塞(Anthony Albanese)身后的那位身材娇小、黑发黑眼、身着彩色服装的女士。阿利是一个积极的倾听者。她点头。她大笑。她会皱眉,也会发出嘘声。

阿莉的衣着总是无可挑剔,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她在堪培拉和珀斯之间无休止地飞行时,将钩针编织作为一种冥想和修心养性的方式。
她参加午餐时穿的白色毛衣是手工制作的(还有一条配套的裙子),参加今年仲冬舞会时穿的钩针编织长裙也是手工制作的。她已经开始筹备明年的舞会,舞会上将会有一朵朵钩针编织的花朵,每一朵花都是独一无二的,代表着这一年中死于家庭暴力的每一位女性。
“她说:”然后,我将把它拍卖给一个家庭暴力慈善机构。
阿利也有自己的家庭暴力故事,她在 2018 年出版的自传《找到我的位置》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从开罗到堪培拉–一个不可抗拒的女人的故事。
她很年轻就结婚了,20 岁时就回到埃及生活,当时她正在学习英国文学,辅修表演。她的婚姻并不是包办婚姻,对她这样的女孩来说,包办婚姻很常见。相反,这是她摆脱穆斯林国家单身女性束缚的一种方式。
“婚姻给了我自由,这是我在父母的屋檐下生活所没有的。它给了我在埃及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已婚妇女的自由。这意味着我可以和朋友去露营,可以参加派对,可以在想回家的时候回家。
有一些红色信号被她忽视了,或者说她并不了解情况。
但搬到珀斯后,暴力和蔑视行为不断升级。
“我有点殉情的感觉。但是,人们对女性幸存者有很多刻板印象,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高成就者。责任感和屈辱感;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更高,”她说。
“我记得有一次开车离开时,我大声对自己说:’你一定就是那种会被男人打的女人’。我已经认命了。
“我把家庭暴力形容为你身体某处骨头上的裂缝,你会终生伴随着它。
“很难想象当时的我是什么样。现在的我比那时的我更像我自己”。
在漫长的六年后,她终于把他赶出了家门,开始了下一个篇章,成为一个破产的单亲妈妈,抚养两个年幼的儿子卡里姆(Karim)和亚当(Adam)。他们是在读了这本自传后才知道自己的虐待史的。
为了维持生计,她做了一连串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然后又回到了她的安全空间:教育。她总共拥有四个学位,包括教育硕士和反恐与安全博士。
回过头来说,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会说自己患有不恰当的多动症,因为我在 9 个月内完成了为期两年的硕士学位,又在两年内完成了博士学位–这通常需要 4 到 7 年的时间。
“我让孩子们上床睡觉,学习到凌晨三四点,然后早上七点起床”
之后,她成为世界知名的研究员,并最终成为专门研究打击网络暴力极端主义的教授。这也让她受邀前往牛津大学和白宫发表演讲。
她的政治火花是在全球反穆斯林情绪高涨之后被点燃的,她在珀斯郊区目睹了太多随随便便的种族主义事件,并因其反恐研究员的身份而成为死亡威胁的目标。
“她在自传中写道:”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被这一切击垮了,被死亡威胁和’把(她)吊死在树上’、’用猪血淹死她’和’把子弹装进袋子里’的呼声击垮了。
大学在一年内两次将她的团队搬到不知名的办公室,并严格要求不得透露地点。
我为午餐预留了 90 分钟的时间,但一个小时后,一位工作人员拍了拍阿利的肩膀,说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来收尾。
天哪,我们甚至还没说到第二任丈夫,或者说第三任丈夫戴夫-艾伦(Dave Allen)。(戴夫-艾伦是加拿大出生的前冰球运动员、警察和情报官员,她在西澳公共服务部门工作时认识了他,并于 2012 年结婚)。
我们需要更多地讨论儿童保育问题,讨论大型营利性公司是否在哄抬物价,讨论市场为何失灵(以及如何应对)。
我们需要谈谈作为女性在议会大厦工作的经历,以及她是否目睹或遭受过厌恶女性或性别歧视的行为(她有)。
十分钟后,肩膀又被拍了一下。她真的得走了,她的下一个约会还没有着落。
我觉得有点被骗了。这真是一顿愉快的午餐。下次我再来珀斯时,一定要去她家门口吃柠檬鸡肉卷。
首发于UNILINK官微 | 微信 AlexUnilink 电话 +61 2 8971 9963 | 提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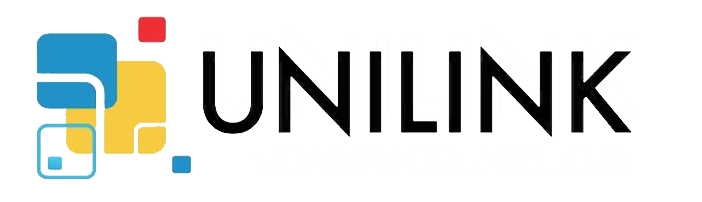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