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型而非转型型:巨型大学的崛起
Chi Baik教授是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该中心20年来一直对全国各地一年级学生的经历进行调查。白智说,到2014年调查结束时,反应正在向南发展。
“她说:”说他们对他们的机构有归属感的学生比例有非常明显的下降。她说:”大学的经验已经变得更多的是交易性的,而不是关系性的,”Baik说。
“真正高质量的经历将更多地是一种深度参与的体验和转变,不仅仅是通过认识新朋友,而是与你所学的东西进行深度互动,并有时间对自己进行反思。”
高等教育有三个主要的政策变化,使其达到今天的水平。
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霍克政府时期,高级教育学院与大学合并,形成所谓的 “统一部门”。与此同时,学费在15年后被重新引入,作为使政府能够为更多学生创造更多名额的手段。它起了作用。学生人数从1989年的441,000人增长到2008年的1,067,000人。
第二个政策变化是在2010年,陆克文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审查实施了所谓的需求驱动系统,允许大学在他们认为能够完成课程的情况下招收尽可能多的学生。其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年轻人的参与率,达到人口的40%。同样,它起了作用。数字从2010年的120万增长到2021年的160万。
第三项政策是大学教育的国际化。这也是由霍克政府推出的,作为向大学提供新收入的一种手段,以减轻政府财政的压力。同样,它起了作用。巨大的成功。学生人数从1985年的16,000人增长到2019年的96万人。
最终的结果是,在2023年,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之一。莫纳什(86,000名学生)、墨尔本(54,400名)、悉尼(75,000名)和新南威尔士大学(62,000名)。与哈佛(23,000人)、普林斯顿(8,600人)、牛津(26,500人)和剑桥(21,600人)相比。
2001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部门有842,183名学生;到202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622,867人,增长了92%。
年度学生体验调查取代了由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进行的第一年体验调查,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相关性:机构越小,学生体验越好。反之亦然。
位于纽卡斯尔郊区的小型五旬节教派大学Avondale,经常收到学生对其体验质量的最高评分。邦德大学是黄金海岸的一所私立大学,收取全额费用,珀斯的埃迪斯科文大学和阳光海岸大学也表现良好。
历史学家Hannah Forsyth博士的《现代澳大利亚大学史》一书详细介绍了该部门的演变,她说,该部门的大规模化,尤其是在过去20年里,创造了她所说的 “大学工业综合体”。
“这是关于钱和更多的钱。大学不断向政府伸手要更多的钱,说他们的资金不足。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将资金从教学转向研究,因为研究是声望的所在。他们从教学收入中交叉补贴研究,因为研究可以转化为更高的排名,从而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Forsyth说。
以澳大利亚排名最靠前的大学–墨尔本大学为例。虽然它无可否认是澳大利亚最受尊敬的机构,但学生的想法却不同。2022年,在澳大利亚139所高等教育机构中,它的学生体验质量排名最后。
莫伊拉-内格雷恩(Moira Negline)并不孤单,她认为自己的大学经历并不出众。
“墨尔本的排名和声誉绝对是我们都知道的。如果老师认为你在学校会做得很好,他们会把你推向墨尔本,”Negline说。
墨尔本大学校长(国际)迈克尔-韦斯利教授说,已经制定了一项战略来解决令人震惊的学生体验反馈问题。但在他的新书《国家的心态》中,韦斯利阐明了现代澳大利亚大学中存在的困难的矛盾。
“澳大利亚人往往在潜意识中对大学抱有这样的理想,认为它是一个超凡脱俗的高等教育场所。然而,它也是一个产生证书的地方,所以人们可以找到工作,”韦斯利告诉AFR周末。”这在人们上大学时的经历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大学是非常大的机构,倾向于让学生匿名。
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加拿大甚至新西兰不同,有通勤大学–学生去离自己邮编最近的大学。
“因此,人们与大学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转瞬即逝和交易性的,而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里,这种体验更多是居住和沉浸式的,”韦斯利说。
他指出,政策环境有利于致力于大规模教学的商业模式。事实上,唯一真正的寄宿制大学是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该校约50%的本科生住在寄宿学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规模也更小,更贴心。它的学生与员工比例为11:1。除邦德大学和斯威本大学外,澳大利亚所有其他大学的学生与教职员工的比例至少是这一比例的两倍,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的比例高达36:1。
“毋庸置疑,财政上最稳健的大学是那些非常大的大学,”韦斯利说。”我认为在过去几年的任何阶段,大学都没有停下来思考,更大的数字可能意味着他们应该改变他们的教学模式。这几乎是默认发生的。大学有5000或10000名学生时的教学模式已经简单地被重新用于拥有50000或70000名学生。”
韦斯利计算过,如果将学生总数除以澳大利亚的大学数量,平均每所大学有36,579人;同样的计算显示,英国有13,740名学生,美国有4,500名学生。
这种规模的副作用是学生体验不佳。Gonclaves列出了一长串有理由的抱怨。

“说实话,我觉得很可笑,因为我在莫纳什大学的学习期间收获甚少,所以在结束时我将获得一个学位,”冈卡尔维斯说,”[也许]我进来时的期望值很高,但这种经历与我想象的有很大不同。
“我在国外(苏塞克斯大学)的学期,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参加亲自授课和辅导,全班同学都积极参与并讨论课程材料。”
冈卡尔维斯说,有点讽刺的是,在与《非洲周末》交谈后,她发现自己被选中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进行实习,该组织隶属于联合国难民署。”她说:”所以,我想我在莫纳什大学的学习终于有了一些积极的收获。
回到墨尔本大学,校长Duncan Maskell上周告诉员工:”我认为,绝对有必要让教育格局的一部分必须由像这样的大学组成,这些大学有明确的使命,为学生和毕业生提供深厚的知识基础,我们可以帮助人们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这里对那些可能与经济成功没有明确或直接关系的想法和概念进行严格和激烈的辩论。”
马斯凯尔曾深情地谈到他在剑桥大学担任全额奖学金学生时改变了他的生活。”它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并向我介绍了许多我甚至没有想过的新事物,”马斯克尔去年告诉AFR。
韦斯利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在昆士兰大学作为住宿学生的那几年,当时该校只有2万名学生,对他的成长很有帮助。但与他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该大学只有4000名学生。
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墨尔本大学的住宿学院生活,希望他们能找到这种经验的影子。
福赛斯说,她在20世纪90年代在悉尼大学读本科的岁月是 “惊人的”。她补充说,”那里有知识和社会参与”。一个辅导班最多只有12名学生,人们深刻地意识到,玩耍和实验是可以的,”扩展我们思维和想法的边缘”。
Baik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墨尔本大学攻读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度过了一段彻底的美好时光。她的三个女儿都有一个相当没有灵魂的、令人沮丧的经历。对她来说,当她转入一个较小的研究生课程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她惊讶地发现,她在正确的地方找到了自己,有了强烈的归属感。
韦斯利说,现在是大学回归本质,将教学和经验作为其任务中心的时候了。
“我认为每个人都期望我们提供与我们作为大学的质量相称的学生体验和教育体验。而且,大学里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袜子。”
首发于UNILINK官微 | 微信 AlexUnilink 电话 +61 2 8971 9963 | 提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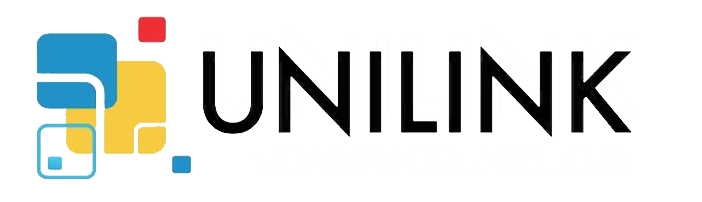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