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领导力奖授予伊丽莎白-纽的开创性工作
2022年AFR高等教育奖的所有八个奖项的获奖者现已公布,该奖项旨在表彰和庆祝澳大利亚大学在过去一年中的杰出努力。
这些类别包括社区参与;新兴领导力;就业能力;行业参与;机会和包容;研究商业化;以及卓越的教学和学习。
这些是AFR高等教育奖新兴领导力类别的入围者。
伊丽莎白-纽教授
悉尼大学化学教授Elizabeth New用一个有趣的比喻来解释她的工作。”想象一下,你有一个非常凌乱的房间,你需要找到你的手机。

“你不能仅仅通过寻找来找到它,你需要你的手机来告诉你它在哪里。所以你打电话给它,声音会告诉你它在哪里。
“同样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像身体或像环境这样的复杂系统,当我们想找到一种可能导致疾病的化学品,一种有毒的化学品或正在做一个真正重要的生物功能。”
New的工作允许这些化学品通过与一个发出光的分子相互作用,向其环境发出信号。无论光在哪里发出,都会显示出分子的位置。
“我们的重点是氧化应激,这是一种氧化剂的过度积累。

“能够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被应用于这么多不同的情况,这真的很令人满意。”
小新开发的一些传感器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她与其他科学家进行了广泛合作。
“我们很想看到它们是有用的。因此,它们已经免费提供给世界上几乎所有使用它们的人”。
目前,纽正在进一步开发她的医学研究工具,包括为接受过铂金化疗的病人进行简单的诊断测试,因为铂金化疗有可怕的副作用。她还在开发一种用于诊断帕金森症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药剂。

米歇尔-肯尼迪
米歇尔-肯尼迪是一名维拉朱里族妇女,也是纽卡斯尔大学负责土著战略和领导的助理院长。
她的工作涉及将土著研究方法应用于健康研究,特别是支持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妇女在怀孕期间戒烟。她是今年新兴领导力奖的入围者。
“我的研究体现了土著人的认识、存在和行动方式,并将土著人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健康研究。
“它试图重写通常报道的关于原住民的赤字叙述,并由与原住民社区合作、倾听经验和分享故事以推动政策和实践改革的真正愿望所推动。
“我所做的一切旨在提供对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合适的、有吸引力的、最重要的是有意义的健康研究。”
格里菲斯大学
Michael Simmonds副教授
了解血液受物理力量影响的方式,以及血细胞和蛋白质如何因此而改变其功能,是格里菲斯大学副教授迈克尔-西蒙兹的工作重点。
“我的团队专门研究物理压力如何改变血液行为,”他解释说。
Simmonds的工作涉及细胞生物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工程和医学,如心脏手术、灌注和血液学。
“在早期,很明显的是,为了产生现实世界的影响,我需要找到具有不同专长的研究人员,他们是同类的精神。我的首要重点是培养一个吸引研究人员成功的环境。”
他的团队将运载氧气的红血球感知环境的方式与主动调节细胞内过程而不是被动应对外部压力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这是一项让我夜不能寐的工作,原因是正确的。”
西蒙斯的研究正被用于设计下一代的心脏辅助设备和开发体外诊断工具。他还在研究一种罕见的血液疾病的诊断如何影响胎儿的健康,在这个领域,目前的测试方法是有限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菲利帕-卡内莫拉
UTS副教授Phillippa Carnemolla与残疾人、老年人、健康从业者、老年护理提供者和残疾服务提供者合作,探索良好的设计在提供护理的方式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她的工作已被应用于社区住房、支持性住宿模式、专门的精神健康设施设计、经历过无家可归者的住房、老年住宅护理、购物区和地方政府。
卡内莫拉的研究支持更具包容性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特别是为那些接受社区护理的人。
她还与智障人士合作,开展研究,探讨他们对自己居住地和当地社区的看法。
“我长期致力于将智障人士纳入社会和公民活动,并支持他们有权拥有一系列可供居住和接受支持的住房选择。”
苏珊-卡兰
苏珊-卡兰是莫纳什大学的发现早期职业研究员和丘吉尔研究员,她是一名社会学家,研究性别、宗教和歧视的交叉问题。
她探讨了所有这些东西如何影响社会凝聚力。她是今年新兴领袖类别的入围者。
“她说:”在我的社会学领域,领导力要求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一个社会问题,而且要理解它和它背后的动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卡兰即将以丘吉尔奖学金的名义前往英国和美国,在那里她将花一个月的时间会见那些从事反对仇视伊斯兰教和其他形式的偏见(如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前沿和长期工作的人。
“我们的目的是学习他们的专业知识,然后将这些想法带回澳大利亚。因此,明年我将看到如何最好地将这些国际做法转化为本地实施。”
她还将在澳大利亚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澳大利亚人如何理解社会凝聚力进行研究。她将研究这两个群体认为应该如何建立社会凝聚力。
“我将调查澳大利亚穆斯林妇女所做的社会凝聚力建设工作的有效性。鉴于我们知道穆斯林妇女远比穆斯林男子更有可能成为仇视伊斯兰教的攻击和虐待的受害者,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穆斯林妇女可能在对抗仇视伊斯兰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卡兰还将探讨像清真寺开放日这样的项目和举措是否对减少伊斯兰恐惧症和建立社会凝聚力有任何作用。

由悉尼大学理学院的Elizabeth New教授提供。
流行文化经常描绘在实验室工作的孤独的科学家。这种形象既有害又不真实。新兴的年轻科学家喜欢与他人互动,就像他们喜欢追求自己的好奇心一样,他们可能会对这样的职业望而却步。
当然,现实情况是,在科学界和学术界的成功都是关于沟通。而沟通是关于人的。科学工作是由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进行的,通常跨越许多国家和许多不同学科。
教导下一代的科学家需要与学生进行有效的互动。而要确保发现具有影响力,则需要与科学和学术界以外的人沟通。
关于成为 “科学领袖 “意味着什么,有很多讨论。
我认为产生一个单一的定义是无益的,因为事实上科学领导力包含了许多不同的领导活动。
科学领袖应该是一个思想领袖:不仅开展世界领先的研究,而且更广泛地领导和影响该领域。通常,研究领导者的影响远远超出学术界,因此,他们必须领导将其工作转化为产业或政策。
科学领袖是人的领袖,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研究小组,还是合作的努力或更大的组织单位。学术界可能是公共辩论的领导者,为政府和行业提供建议。
但是,这样的广泛性可能会让人疲惫不堪,并可能导致学术界的压力,即他们必须擅长一切–在媒体上露面、政策制定、社交媒体和行业参与。
我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学术界做他们擅长的事情上。毕竟,大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机构,每个部分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作出贡献。
早期职业生涯的学者参与许多不同的活动有很大的好处,但目的是确定他们的优势和激情所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有效地发展这种广泛的领导素质?传统的博士生培训模式是一种学徒模式。当导师本身只接受过开展研究的培训时,这种情况就会自我延续。在我从事学术工作的10年中,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方面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博士毕业生必须培养的素质远远超过他们自己项目的专业知识。例如,在悉尼大学,博士生和他们的导师被要求讨论如何解决11个研究生研究素质的问题,包括文化能力、影响力和参与度:只有一个提到了深刻的学科专长。
如果我们要考虑到我们不仅仅是在培养未来的学者,而是培养我们社会未来的领导者,他们是科学家–无论他们是否直接从事科学工作,这都是关键。
学术界发生的另一个令人振奋的转变是更加注重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紧密结合。
这一点通过新的国家产业博士项目和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正在推出的新的产业奖学金项目就很明显。通过与来自学术界以外的领导人接触,我个人学到了很多关于领导力的知识。
通过参与西太平洋学者信托基金,我有机会做到这一点:观察西太平洋银行和其他组织的董事会和C-suite成员如何领导和互动,扩大了我对领导风格的看法。
我很高兴,通过更广泛的产业-学术接触,许多其他早期职业的学者将有类似的机会向大学以外的世界学习。
在我从事学术工作的第一个十年里,看到大学认识到培训和挑选学者成为领导者的价值,这让我感到很新鲜。
大学部门的下一个挑战是确定学术界如何能够在正常工作周内成为有影响力的领导者,而不需要投入数小时的加班。
这是该部门亟需的模式转变。我希望,当我再过十年回想起来时,我将为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振奋,并希望凭借我所掌握的领导技能,我能够成为这一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首发于UNILINK官微 | 微信 AlexUnilink 电话 +61 2 8971 9963 | 提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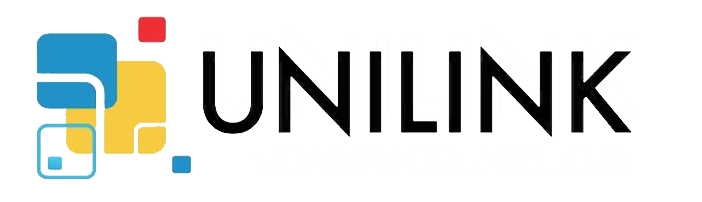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