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CEO为何对与《金融评论》共进午餐持谨慎态度?
杰克逊一直很低调。她在澳大利亚大学网站上的页面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只有一张头像和最基本的姓名、职位联系方式。即使是她的服装,一套蓝色羊毛套装和一件初级格子衬衫,似乎也是为了不引起注意而选择的。
在午餐前,我意识到我以专业身份认识杰克逊已经16年了。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她开始担任工党维州左派的中坚力量金-卡尔的媒体顾问时。我们的职业生涯并行不悖–我是一名记者,她在政治、通信和宣传方面的发展轨迹。但我对她一无所知。
所以我谷歌了一下她。同样,没有什么。LinkedIn、Twitter、会议项目、旧工作的数字遗留物。我继续挖掘。最后,我找到了她2013年在国家博物馆发表的一篇演讲的记录。这次活动被称为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妇女”,而且是在她担任澳大利亚科技部首席执行官的第一个主要宣传角色之后。这就像撞到了金子的缝隙。
“谈论自己不是我的强项,”杰克逊说。”谈论事情是好的。我真正喜欢做这项工作的公共宣传部分,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论据可以运行,而我喜欢一个结构良好的论据。”
在午餐期间,我发现有两件事让杰克逊很兴奋:大学和食物。在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一直是《堪培拉时报》和《悉尼先驱晨报》的《美食指南》的食品评论员,但几年前终于放下了。
“她说:”当我转到这份工作时,我就不再做了,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公正地做这件事。
杰克逊选择Locale有两个原因。”它就在办公室的拐角处,我喜欢他们的比萨饼”。
杰克逊是个纯粹主义者。围绕食物有应该坚持的规则。
“我从来不在午餐时间出去吃,”她说。”就我而言,在外面吃饭是为了吃晚饭”。
事实证明,晚餐不会被破坏,因为杰克逊只处理了两片半她出色的意大利熏火腿和芝麻菜比萨。
点餐时,我问杰克逊关于披萨上的菠萝。她被吓坏了。
“菠萝在比萨饼上没有位置,”她说。”这是一条硬性规定”。
但它是焦糖的,新鲜的菠萝,我反。
“她说:”如果你想对披萨进行创新,那就去做吧。
“你会苛责我吗?”我问。
“我会评判你的,绝对的。”她说,然后迅速收回了答案。
“我当然不会。只是菠萝在比萨饼上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澳大利亚化,这种东西是高贵而美丽的,不应该被菠萝所污染。”
我选择了纳波利塔诺。
我问她的父母是否是美食家,她是否在那些在大盘丰盛的食物和酒瓶上进行不朽的讨论和辩论的家庭中长大。
“两人都对食物感兴趣,我和祖母一起学习烹饪。食物一直是我觉得有无穷魅力的东西。”
我问她是否有喜欢的名厨。她对这个概念感到震惊。那么,她喜欢做谁的食物?
“我非常尊重像伊丽莎白-大卫这样的人,”杰克逊说。”还有,离家近的罗斯玛丽-布里森登,[ABC记者]迈克尔-布里森登的母亲。她写了第一本真正严肃的关于东南亚食物的书,在澳大利亚出版。”
然而,大卫是她的最爱。”她的文章也写得非常漂亮。你可以阅读她的书,真实地了解她所品尝的所有东西和她所看到的所有东西。与其说是名厨,我欣赏的是那些能够打开冰箱,用里面的东西做出美妙的东西的人。”
她形容自己是个好厨师,喜欢保持简单。
“她说:”我当然不会出去买17000种精制原料。
那么你今晚准备做什么饭呢?
“我将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有什么。

杰克逊的食品写作生涯始于20世纪80年代她在拉托布大学读书时,在那里她在名人罗伯特-曼恩和朱迪斯-布雷特的指导下学习政治和哲学。她在学生报刊《拉伯雷》上开设了美食专栏。
“我不确定其他编辑对此有何感受。我认为以前学生报纸上从来没有过食品专栏。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回应。”
杰克逊曾经得到过这样的建议:如果她想作为一名记者被认真对待,她应该远离食品评论。
“她说:”我很认真地忽略了她。”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食物是我认为非常严肃的东西,是我们文化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那些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东西之一。我发现它在智力上令人难以置信地有趣。”
杰克逊和她的小妹妹在墨尔本埃尔瑟姆的一栋泥砖房中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她的父亲,哲学家和学者弗兰克-杰克逊,是一位哲学家的儿子。她的母亲莫拉格-弗雷泽(Morag Fraser)曾是一名学校教师,编辑公共事务-艺术-神学杂志《尤里卡街》达十年之久,在文学界享有盛名。她是美国广播公司前记者莉兹-杰克逊的侄女。
当我暗示她的父母–他们是由加雷斯-埃文斯在墨尔本大学介绍的,他们都是学生–是 “知名人士 “时,她不寒而栗。
“我的父母从来不会把自己描述为杰出的人,”她说。”他们是有严肃成就的人,他们努力工作”。
勤奋工作是我们不断回到的一个话题。
她谈到她作为劳工部参议员金-卡尔的顾问的七年时间是刺激和兴奋的,但也很累。早上7点到达办公室已经很晚了。12个小时的工作是松懈的。
“我在政界工作的那七年,我比以前或以后学到了更多关于权力的行使和政治如何运作的知识。我学会了比以前或以后的工作更努力地工作。但我再也不会回去了。它太难了。”
杰克逊和卡尔在职业上有过交集,当时她是《堪培拉时报》的一名教育记者。她报道了他在参议院的估算,以他标志性的方式询问紧张的公务员–一部分是大锤,一部分是手术刀。当他为她找了一份工作时,这似乎是一个好主意–她可以在某个地方将政治理论付诸实践。
也是在《堪培拉时报》,她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安德鲁-弗雷泽。他是她的老板。他们把自己的感情藏在心里,然后在她搬到墨尔本与卡尔一起工作的前夕,两人都承认了他们的相互吸引。
三个月后,她把行李塞回卡车,回到了堪培拉,开始了与弗雷泽的关系和堪培拉泡沫内的生活。
不知何故,在按照折磨人的时间表工作的同时,她生下了两个孩子。
“托儿所是个很好的东西,”她死皮赖脸地说。”安德鲁在第一次婚姻中有过孩子,所以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我有几年没怎么睡觉。这已经到了一个几乎不可持续的地步。但你只要继续努力,就可以了。”
杰克逊喜欢大学。
她说:”它们是非同寻常的地方,充满了非同寻常的人,”她说。”它们是人们围绕着想法走到一起的地方。这是一个你可以真正磨练你的想法和挑战自己的环境。
“2020年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是走进一个校园,而校园里没有人。”
杰克逊说,她希望她能在隧道的尽头看到国际学生回归和该行业重启的曙光,但她无法做到。
“大学里的问题不是一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两年、三年和四年的问题。我们去年损失了18亿元的收入。我们的预测是,今年我们将损失20亿元。”
大学被指责沉迷于海外学生对学位的看似不可阻挡的需求所带来的轻松资金,这些资金被用于研究和改善校园以达到国际标准。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提高了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排名,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学生。然后,COVID-19出现了,这一切都开始像纸牌房子一样摇摇欲坠。
杰克逊在几个方面都受到了压力。作为前工党工作人员,她在2018年的任命被一些人视为澳大利亚大学获得不受限制地进入预期的联邦工党新政府的机会。工党输了。
与联盟政府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很僵硬。在文化战争中的紧张关系,如人文学科的研究拨款和言论自由,已经主导了对话,而该部门似乎无法将其作为国家资产来起诉。
资金削减和敌对的政策变化已成为常态。围绕JobKeeper的规则被修改了三次,其明确目的是将大学排除在该计划之外。
在澳大利亚大学的总部,校长们试图发动某种政变,并强迫对该组织进行内部审查。
由此产生的报告建议,除其他事项外,”加强首席执行官的作用”,并让他们更多地参与高峰集团的活动。
我问杰克逊,她是否对这篇评论感到不安。
“只是让我绝对清楚为什么和如何建立审查,因为媒体上的一些东西是不真实的,”她说。
“我们委托进行审查,因为这是良好治理的一个常规部分。”
她说,在过去的18个月里,包括澳大利亚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物–大卫-冈斯基、朱莉-毕晓普、凯瑟琳-利文斯通、马丁-帕金森、彼得-瓦格斯和贝琳达-哈钦森等人在内的校长们比以前更多地参与到宣传活动中,”这是一件好事和有益的事情”。
我们的盘子被清理掉了。我的是空的,杰克逊的几乎没动过。
服务员问我们是要甜点还是咖啡。
“甜点将是一种犯罪,因为我还没有吃完我的比萨饼,”她说,选择了一个短黑。我买了一杯玛奇朵。
当采访结束时,我告诉她,我很高兴我没有得到带菠萝的比萨饼。
“这让我很高兴,朱莉,你看到了你要犯的几乎是灾难性的错误的明智之处。”
这句话是阿门。
Catriona Jackson是8月16日《金融评论》高等教育峰会的主讲人。 live.afr.com/Higher-education
Locale Pizzeria, Shop 5, Hopetoun Cct, Deakin, ACT
那不勒斯比萨饼,24元普鲁士比萨饼,24元咖啡,4元玛奇朵,42元一瓶圣佩莱格里诺气泡水,17元
共计:73元
首发于UNILINK官微 | 微信 AlexUnilink 电话 +61 2 8971 9963 | 提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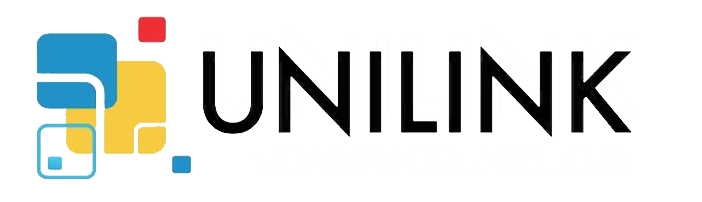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